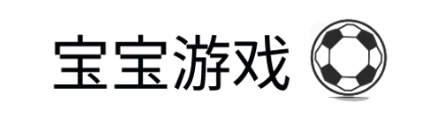阿来《云中记》如何将一个人的返乡之旅谱写出一曲庄重"安魂曲"?

一,阿来《云中记》如何将一个人的返乡之旅谱写出一曲庄重"安魂曲"?
要想真正地理解阿来最新长篇小说《云中记》中所讲述的一个人的“安魂”故事,无论如何不能忽略央金姑娘与中祥巴这两个后来才出场的人物形象。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陪衬,才能够更好地凸显作家阿来根本的写作意图。
漂亮的央金姑娘,虽然酷爱跳舞,但却很不幸地在地震中失去了一条腿。一条腿的失去,对于一位依靠身体才能够表演的舞者来说,可以说是一种足以致命的打击。但就是这位曾经为了自己失去一条腿要死要活的姑娘,五年后却突然出现在了只有阿巴一个人的云中村。
回到云中村,或许与触景生情的精神刺激紧密相关,央金姑娘的舞者本能突然间爆发了:“姑娘身体的扭动不是因为欢快,不是因为虔诚,而是愤怒、惊恐,是绝望的挣扎。身体向左,够不到什么。向右,向前,也够不到什么。手向上,上面一片虚空,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供攀缘。单腿起跳,再起跳,还是够不到什么。于是,身体震颤;于是,身体弯曲,以致紧紧蜷缩。双手抱紧自己,向着里面!里面是什么?温暖?里面有什么?明亮?那舞蹈也不过两分钟时间,只比当年惊天动地的毁灭长了不到一分钟时间,姑娘已经泪流满面,热汗和着泪水涔涔而下。”
但祭师阿巴根本想不到,这次突然回到云中村的央金姑娘,却并不是因为怀恋故土惦记亡者而来。在她的背后,潜藏着的是一种资本的力量:“她已经签约了一家公司,一个摄制组悄无声息地跟在后面。公司要包装一个经历了大地震,身残志坚的舞者。这次回家,是了姑娘的心愿,同时也是为下次参加某电视台的舞蹈大赛准备故事,一个绝对催泪的故事。这件事姑娘自己知道,阿巴和云丹不知道。姑娘为此有些小小的不安。”
到后来,央金姑娘果然为以如此不恭态度对待故乡深感不安,陷入自我矛盾的状态中。或许与央金姑娘面对故乡时的心生愧疚相关,此后她尽管想要重新抵达那次在故乡舞蹈的境界,但却再也未能如愿以偿。只有她彻底摆脱了签约公司控制,并拥有乡亲们的亲情簇拥后,央金姑娘方才重新找到了跳舞的感觉:“她的舞姿变得柔和了,柔和中又带着更深沉的坚韧和倔强。”
阿来在长篇《云中记》开篇的自白,小说如庄重而悲悯的“安魂曲”,献给“5·12”汶川地震中的死难者和那些消失的城镇与村庄——文本叙事极富诗意,是“边地书、博物志与史诗”,更是从近处历史所生发的宏阔如空山的回响。
《云中记》集中塑造了苯教非遗传人阿巴这一人物形象——阿来将其作为主要的叙事策略——以时间及其节奏性为章的长篇文本结构中,小说细数了阿巴从移民村重回地震灾区云中村的半年时光,阿巴在遗迹中寻找旧人留存之物度日,以特有的“告诉”方法和“祭祀”仪式安抚、祭奠、超度灾难中逝去的乡亲,不单是这些情节写得细腻悲壮,与这一切关联的万物万灵都被一股巨大的情感涡流席卷,而随着阿巴不断深入灾区、直面生死、思考灵魂与信仰,他最终以自我生命和全然纯粹的灵魂献祭深爱的故土——此之消亡走向彼之回归,读者在多重的命运选择中体悟“安魂”的复杂深意,而这,也告慰生者。
在《云中记》开篇便能捕捉到阿来近年来颇受关注的非虚构写作:作为区域地理象征的岷江水和如今作为新地标的移民村们,已经被更为宏阔的历史感裹挟;“他叫了一声山神的名字”——我始终铭记在最初的那一秒钟是如何意识到这是地震的爆发;“当他们看到江边公路上那些等待转运灾民的卡车时,一些人开始哭泣,像在歌唱”——后知后觉的悲伤再次为灾难的巨大和突如其来做证,多少人如那颗老树般宁可“死意已决”;再后来,相信所有读者都曾在新闻里看到,解放军、医疗队、救灾物资和重建规划……
阿来的“安魂”直面记忆和现实,非虚构笔法和细节的真实不乏史书实录之感,这亦与小说围绕藏地文化、安魂须仰万籁相通。于是我们在小说里“俯察品类之盛”又广识“草木鸟兽虫鱼”以赋比兴,连同诸多民族文化习俗,关于圈养还是跑山放养,关于饮酒,关于碰头礼和“告诉”,关于抖开袖子袖管里比划手势议价,形成了文本融贯的文化气质风貌。也正因了此种风貌,阿来独有的幽默感才有的放矢:始终喊不对自己称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老子是汉族大哥”等细节透露的名实之辨和荒诞的英雄感;阿巴对作为“政府的人”的侄子的为难和体恤;云中村人不会唱的《感恩的心》和加上的哑吧比划动作;地震遗迹摇身一变成为骑马上山看的风景和如今包括收费厕所在内的景区价格乱象……这些源自作家悲悯心的幽默感关涉无处安放的自我认知焦虑,存乎整体与局部、宏观与微观、政府关心的受灾群体和各不相同的灾民个体生命之间。
这场“安魂”,与阿来的历史感和对当下的关怀相系,小说以民族血缘为纽带建构文本稳固的伦理传统,同时将以之为基础的藏族乡村生活中民族精神空间和文化心理结构中的裂变、阵痛和盘托出,“安魂”成为重要的历史时刻和现实节点,对阿来而言也是人与乡之间无法隔绝的血脉。由此,小说主人公阿巴的信仰在一己执念之外生发出坚实的合理性、正当性与必要性,小说的边地书、博物志性质亦是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史载。不妨细数由己及众的“安魂”层次:阿巴的自我回归和以身殉乡情、重拾旧日程和记忆重演——祭祀山神阿吾塔毗、云中村招魂和安抚亡灵——以及生者各自生活的告慰和延续。总之,“不让悲声再起”,就需要精神枷锁的逐层开释,“天与地”“神与人”互相感知,我们从中看到了如《格萨尔王》般的藏族英雄个性化“重述”和现代性视野,关于生死灵魂处境的讨论在理想信仰与文化的场域中成为一场“相信”的哲学思考和信念转化,这些同属于阿来的生命理解系统,当阿巴践行了这种应对苦难的精神,苦难者就会“复活”。
《云中记》颇致力于画面感及其真实性的建立,此即阿来对历史性灾难创伤的正视和呼吁:共同的“安魂曲”并不仅是局部或区域性的记忆重拾。阿来使世人再度面对那个悲惨的灾难性时刻的前世今生,呼唤他们去努力寻求可能的解决之道,去留意、体悟他人的苦难——通过文学创作的艺术呈现抵达广泛的深入的持续响应,阿来必须为读者提供一幅幅可感可想可见的画面去超越时间和历史的目击时刻——对灾难的承认、再现与和解,构成谱写“安魂曲”的创作动因与可能。
事实上,无论亡灵与鬼魂的出现与否,都无妨阿巴在云中村认真地履行自己身为祭司的职责。从根本上说,对於阿来的这部《云中记》来说,最重要的核心情节,就是祭司阿巴的毅然重返云中村。在时过境迁十年时间,公众差不多已经把当年的汶川大地震都遗忘殆尽的时候,阿来却借助於祭司阿巴一个人的返乡之旅而谱写了一曲莊重而悲悯的「安魂曲」,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绝对不容低估。很大程度上,也只有到这个时候,我们方才能够明白《十月》杂志的编者何以会如此评价阿来的《云中记》:「一位为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被命名的祭司,一座遭遇地震行将消失的村莊,一众亡灵和他们的前世,一片山林、草地、河流和寄居其上的生灵,山外世界的活力和喧嚣,共同构成了交叉、互感又意义纷呈的多声部合唱。作品叙事流畅、情绪饱满、意涵丰富,实为近年来不可多得的力作。」诚哉斯言,能够把《云中记》这样一部一个人的「安魂曲」,最终演变为内容意涵特别丰富的多声部合唱,所充分见出的,正是作家阿来精神深处那样一种特别难能可贵的历史责任感与人道主义情怀。
这都是一段故事
总结:以上内容就是宝宝游戏提供的阿来《云中记》如何将一个人的返乡之旅谱写出一曲庄重"安魂曲"?详细介绍,大家可以参考一下。